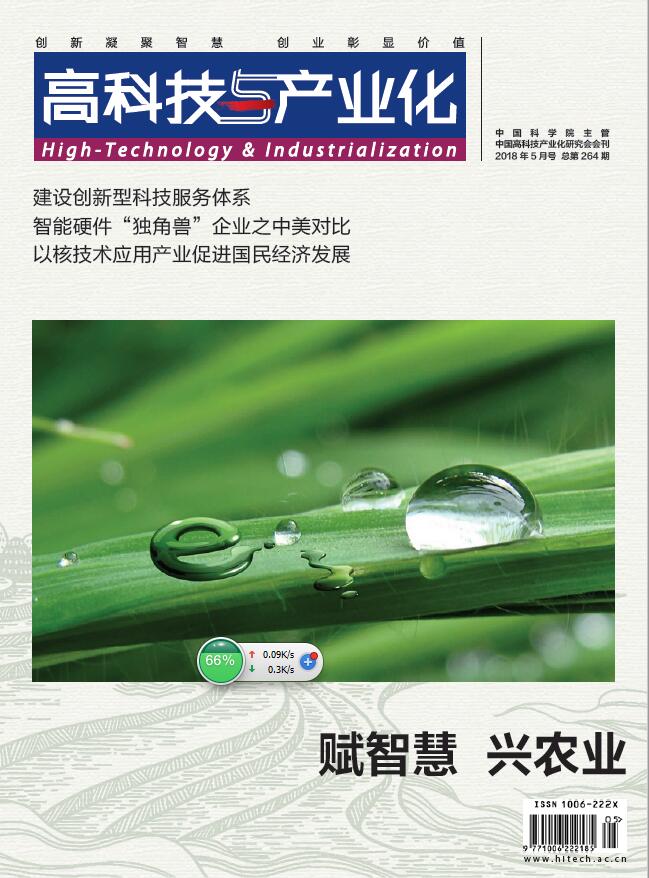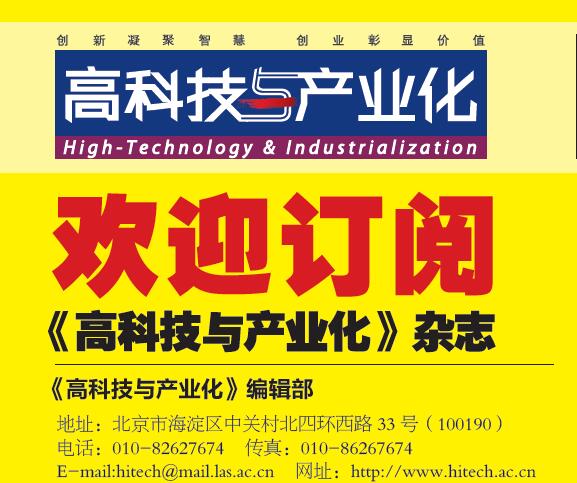哲学对科学究竟有没有指导作用?

哲学流派影响科学发展方向
有人说,哲学对科学没有指导作用;更认为,如果哲学自认为对科学有指导作用,那末,这只不过是显示了哲学自身的狂妄、愚妄。我的观点是,哲学对科学有指导作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指导作用,除非人类的精神领域不再有哲学——但对人类的精神领域来说,没有哲学是不可想象的,至少现在还不可设想。
哲学对科学的指导作用,就其价值特征而言,无非是两种情况:积极的指导作用和消极的指导作用。对科学起积极指导作用的哲学,首先是唯物主义哲学。被后人称为“自然哲学”的古希腊的物理学,是西方科学的原始形态,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动力和观念基础是朴素唯物主义。
朴素唯物主义指导人们开展古典物理学研究,这对人类的科学发展无疑是哲学对科学所起的积极指导作用。而唯心主义则指导人们开展对人类心灵活动的研究,使他们离开古典物理学研究的轨道,这对古典物理学的发展来说显然具有消极意义,是为哲学对科学的消极指导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对人类心灵活动的研究,却使古希腊智者的论辩术最终发展成为逻辑学,到亚里士多德时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三段论逻辑体系。这个逻辑体系后来一直是人们探索现实世界的重要的认识工具,对于人类的科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从这方面来看,唯心主义对科学的指导作用也不完全是消极的,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反之,如果只在朴素唯物主义指导下去研究自然,而不去研究人的心灵活动,逻辑学便无从产生,这同样会消极地影响到科学的发展。
可见,哲学对科学的指导作用具有双重性,其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相互交织,难以互相剥离。据此可以认为,对科学纯粹起积极作用而无消极作用,或对科学只起消极作用而没有积极作用的哲学,应该是不存在的,除非其哲学不是具体的哲学活动而只是哲学的绝对理念,抑或貌似哲学而实为痴人说梦之类。
哲学对于近代科学的积极指导
近现代科学的思维工具,除了传统的三段论逻辑,更有弗兰西斯·培根系统地加以阐述的归纳逻辑,被培根称作“新工具”的这套归纳逻辑体系,是实证的科学时代科学地认识世界过程中最重要的思维工具,以至于可以说,没有归纳逻辑,就没有近现代的实证科学。
培根的归纳逻辑体系是在唯物主义原则指导下,通过对传统逻辑学以及运用它的逻辑规则,进行唯物主义批判和对人类认识过程中的归纳活动进行哲学的概括和总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里,唯物主义以其对思维“新工具”产生所起的关键作用,再一次显示了它对科学的积极指导作用。
弗兰西斯·培根以其卓有成效的唯物主义哲学活动和“新工具”的发明,使他堪称“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马克思语),以其“新工具”的发明为标志,人类的知识发展开始进入到实验科学时代或实证科学时代。
孔德以后,“范式”(库恩)、“证伪”(波普尔)等科学哲学概念,也都作为科学原则对科学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特别是波普尔的“证伪”概念,它对孔德以来一直流行于科学界的“实证”概念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这两个概念相互结合而形成的科学原则,对进一步规范科学活动和明辨科学是非,从而积极地推动科学发展,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唯物主义看来,“实证”、“证伪”之类的哲学概念当然不是先验的精神实体,而是从关于现实科学活动的经验材料中抽象出来、反映现实科学活动的本质属性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哲学概念以及由这类概念所构成的哲学理论,属于所谓“事后诸葛亮”的“事后之念”和“事后之论”,但是,“事后之念”和“事后之论”不只是哲学概念和哲学理论的特点,而且也是一切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的特点,因为任何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也都不是先验的,而是从关于自然现象的经验材料中抽象出来、反映自然现象的本质属性和规律的概念和理论,但不因其在“事后”,这些概念和理论就对人类的生活和实践不具有“事先”和“事中”的指导意义。
一种新的概念和理论产生以后,起初人们会比较明显地感受到这种概念和理论对自己生活和实践的指导意义,例如,“证伪”概念被提出来以后,它对惯于用“实证”原则来判定科学是非的人们来说,就具有令人感受明显的冲击力,使他们在判定科学是非的时候,也自觉地尝试运用“证伪”原则。
尽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并非总能清醒地意识到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对生活和实践有什么指导意义,但无论其是否具有这种清醒的意识,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都在实际地指导着他们的活动。
只是这种概念和理论在其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已经逐渐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规则,这些规则对他们来说,似乎不再与那些抽象的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有什么联系,而仅仅是其生活常识和习惯的一部分,一些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做法和办法。
哲学概念和哲学理论对科学活动的关系也是如此。从事科学活动的人们也不是总能清醒地意识到哲学概念和哲学理论对他们日常的科研活动有什么指导意义,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们的科研活动就不必受哲学概念和哲学理论的指导。事实上,对某些不能清醒地意识到哲学概念和哲学理论对科学的指导作用的科学工作者来说,他们科研活动中的那些习以为常的某些做法和办法,恰恰就是从一些看起来极其简单的哲学原则经由某些中间环节转化而来。
科学应与哲学“结盟”
哲学对科学的指导作用不容置疑,正如科学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不容置疑一样。否定哲学对科学的指导作用,也必然要导致否定科学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否定科学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实践观上的经验主义;否定哲学对科学的指导作用,则是科学观上的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必然导致拒斥哲学理论而迷信科学知识,单纯地依靠个人科学知识和世代积累起来的科学知识,去从事那区别于哲学科学的常识科学。自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科学界所从事的科学基本上就属于常识科学范畴,即这种科学活动基本上是依靠个人科学知识和西方传入的科学知识来进行。这种科学活动因为自觉或不自觉地拒斥哲学理论而轻视或忽视对既有科学知识进行抽象与概括,因而很难创建关于科学的哲学概念与哲学理论,从而不能为科学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新的科学原则,遂使得中国科学几乎只是也只能跟在西方科学后面亦步亦趋地缓慢发展。
中国科学之所以至今仍然落后于西方,中国科学界从未出现过一位足以称得上科学大师的科学家,其直接原因就在于:中国科学界长期以来一直轻视或忽视对既有科学知识进行抽象与概括,而哲学界则由于人员绝大多数出身于文科而缺乏科学的基本素养,不具备对既有科学知识进行抽象与概括的主观条件,由此导致科学与哲学从来缺乏紧密的互动,实际上长期处于“不结盟”和“各自为战”的状态。
笔者对中国科学与哲学的“不结盟”状态有深切的感受。起初,这种感受仅限于对中国哲学界历史和现状的认知和体验,凭我所见所闻,远的不说,至少自建国以来,中国哲学界长期脱离现代科学,从事哲学的研究者几乎完全只是依靠历史上哲学家的论著和自己的生活感悟来进行哲学研究和哲学创新。
这种脱离科学的哲学当然对科学没有积极的指导作用的——如果说现在中国哲学界的哲学对于科学还有某种积极意义的话,那末,这仅仅是因为被它所继承的历史上的哲学(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本来就包含着一些可靠的、具有普适性的原则(如事实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但是除了这类哲学史上固有的知识内容,它自身并没有对哲学发展作出什么新贡献,它从来不曾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热切关注科学发展并及时概括和总结科学新成果,而是既不关心也无能力概括和总结现代科学新成果。这也是局外人对中国哲学界的哲学普遍抱以鄙视态度的现实根据。
中国科学界出于本国“科学工程”建设的需要,则积极地推动政府出高价从西方引进“高端工程师”和“高端科技产品”,从没有想到要创建中国自己的“科学企业”,发展本国的“科学生产”,并为此而自觉、亦即积极地培养本国的“科学生产者”能够进行科学的哲学创新从而提出新的科学原则的科学哲学家或科学大师,以及能够遵循和运用新的科学原则来进行高科技创新的高端工程师。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
 |
版权:《高科技与产业化》编辑部版权所有 京ICP备12041800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四环西路33号 邮编:100080 联系电话:(010)82626611-6618 传真:(010)82627674 联系邮箱:hitech@mail.las.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