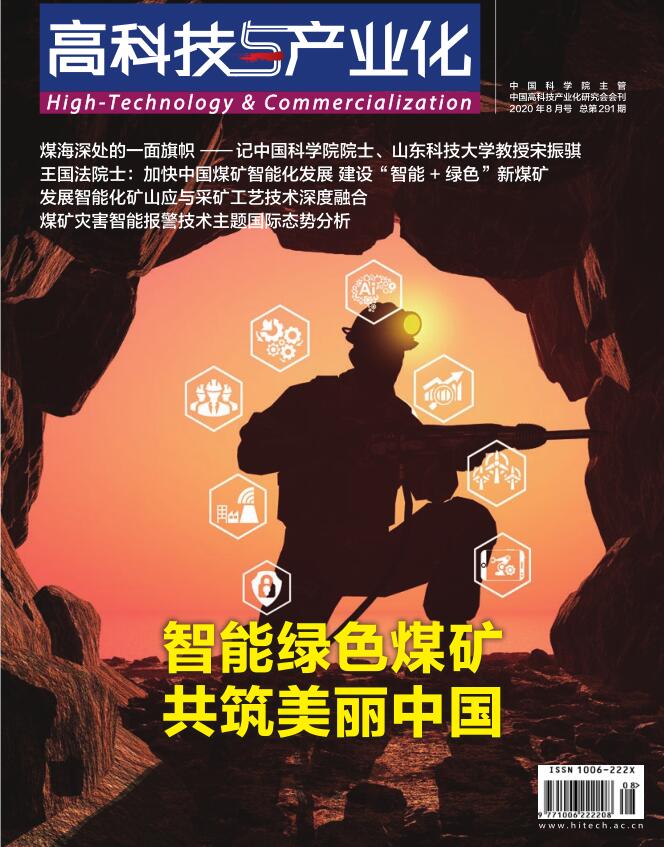蛟龙入海中国载入深潜方兴未艾
7000米深的海底,藏着多少人类未曾窥探的秘密?
看似静谧的幽深海域之下,究竟隐藏着多少危险?
2006年,付文韬万中挑一入选成为中国第一代潜航员;2012年他作为首批潜航员,跟随“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一起潜入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
就在这一年的6月24号,“蛟龙号”下潜突破7000米;同一天,“神舟九号”也与“天宫一号”在浩瀚太空中成功对接。
如今已是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潜航员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载人深潜英雄”的付文韬,忆起当天的场景时说:“那天让我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诗词,‘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可能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让两大壮举在那一天完成。”
深潜区中国进展喜人
海洋面积占地球表面的71%,其中超过2000米深度的深海区占据海洋面积的84%。换言之,地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区域被深海所覆盖。付文韬在“第二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世界海洋科技论坛”中作报告时指出,深海探测的目的包括勘探海洋资源、开展海洋科学及环境保护。
在深海里已发现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锰结核、热液等,能源资源也非常丰富,如可燃冰在中国南海的探明储量占全球一半以上。目前,探索利用深海的设备包括无人潜水器、载人潜水器及有缆、无缆的细分。
付文韬指出,这几种潜水器各有特点,如无人无缆潜水器(AUA)的体型比较小,可以在大范围海洋区域进行调查,对海底地形及其他方面都可以进行大范围的搜索。
相对而言,载人潜水器的作业区域和范围小一些,但它可以对一个几百米或者几公里长的区域进行非常精细的考察。遥控无人潜水器(ROV)则介于两者之间,作业效率相对低一些。
中国是全球第五个掌握载人深潜器技术的国家。“蛟龙号”是我国第一艘完成自主设计、集成研制,并且独立完成海上实验的大深度载人潜水器,促进了中国深海领域工程技术的发展。
在“蛟龙号”此之前,美国“阿尔文号”作业型载人潜水器的下潜深度是4500米,日本“SHINKAI 6500”号的下潜深度为6500米,俄罗斯“和平号”潜水器的深度也达到6000米级。
付文韬说:“‘蛟龙号’的下潜深度在同类型潜水器里是最深的,已经达到7062米。目前可以在全球99.6%的海域进行综合作业。”
“蛟龙号”深潜实验成功后,我国又着手推动了“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的研制。目前“深海勇士号”已经完成了海上实验并已经下潜100多次,下潜深度为4500米,其最大的亮点是90%以上核心部件的系统已实现国产化。
付文韬透露,“深海勇士号”在太平洋西风带下潜时曾取回一组样品——一个直径达1.5米的红珊瑚。“‘奋斗者号’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海上实验,相信明年将成为我国科技工作的一大亮点。”
从2009年到2018年年底,“蛟龙号”共累计下潜了158次,付文韬参加了七十余次。“我特别有成就感的是,下潜大大推进了中国科学界对真实深海世界面貌的认知。”付文韬说。
他透露,目前的作业地点已经包括中国南海冷泉区、太平洋海山区、结合区与深渊区,以及西北印度海的热液区等许多区域。
深海中无处不在的危险
“我是‘蛟龙号’的主驾驶,也是第一批潜行员。很多人以前关注我们是从新闻上看到出征时向大家挥手、致意、告别,下潜成功回来时送鲜花,也因而获得很多荣誉。但其实在我看来,这份工作就是一个高级‘蓝领’,外表光鲜但人们很难看到我们非常辛苦的那一面。”付文韬有点感慨地说。
他回忆道,“蛟龙号”在2009年第一次出海时,母船为4500吨级的科考船“向阳红09”。在他们一行开启科考行程的第二天,就在海上遇到了热带低气压,船晃得非常厉害。
付文韬说:“这是一段很痛苦的经历。在海上晃时单边船体达到了14到15度,对我们刚出海的新人而言是一个非常难受的过程。我就晕得比较厉害,人就像感冒发烧一样。我咨询体能老师后,他告诉我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坚持锻炼,适应力会更快一些。于是我主动去锻炼,虽然做力量练习时头像炸了一样,但是效果非常好。在后来的下潜中,我也发现适应它(周围状况)很重要。”
还有一次,原本半个小时就能回收上母船,结果起吊装置出了意外,付文韬和同行科研人员在海上足足漂了一整夜,在海浪里颠簸了11个小时。
截至目前,付文韬是“蛟龙号”下潜次数最多的潜行员之一。“其实这是挺辛苦的一件事情,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样。但更困难的是,这个工作的显著特点就是它具有很大的危险性。”
他说:“通常我们做实验的时候都会挑比较平坦的地方下潜。深渊区跟普通人想得不一样,并不是笔直下去的一个沟,而是相对比较平缓的4到5度坡度突然陡地下降,然后又是比较平缓的坡再下降。一般我们接触更多的是那段平缓的坡,因为接触面积比较大。但我在2016年下潜时,运气不太好,正好遇到了陡坡的地方。”
在下潜过程中,为了节省能量会将所有设备关掉,一般在距离海底还有200米左右时才会打开灯光。而在2016年这次下潜中,当付文韬想看看距离海底还有多远时,意外发现通过玻璃窗能往外看到东西。
“这是很不正常的。因为我之前已经下潜了很多次,正常状况外面应该是漆黑一片。而我能够看到东西说明,视野范围之内的物体可能距离船仓只有5到6米的距离。”付文韬解释道。
当时“蛟龙号”正在高速下潜,在没有采取制动措施的前提下,每分钟可下潜30米。他们遭遇到的是一个80多度的陡坡,几乎接近垂直。如果继续下潜,潜水器就会挂到坡体,翻滚下去将非常危险。
“我们第一时间就赶紧就抛掉压载把速度降下来,将推力器打开,从背离山体的方向撤了出去。如果晚了一分钟打开推力器,很有可能‘蛟龙号’就这样翻滚而下,后果不堪设想。”
在此之后,付文韬反复地向别的科研人员讲这个故事,提醒大家不要一味根据已有经验下潜,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
科考中需要担当与创新
海洋热液区中的热液可喷发出接近380度的高温热液,而“蛟龙号”第一次下潜热液区时就遭遇了非常惊险的一幕。
如今回想起来,付文韬仍然心有余悸:“当我们靠近热液区时,海底流将热液慢慢吹偏了,我右边的观察窗就这么一直被热液烧着。当时负责右侧窗的科学家因为关注中间的作业情况,忽略了自己负责的区域,我当时也忽略了。等我们反应过来时,右边观察窗差一点就被烧穿,非常危险。”
此外,“蛟龙号”上浮中也有一段令他特别难忘的经历。通常潜水器在上浮时,都会采取减轻自重、抛掉压载体的方式,让其自动上浮而不需要依靠动力。
但有一次,付文韬和同伴临近抛载时,却发现有一侧的抛载无法抛出。而海底与海面海水密度有密度差,逐渐上浮时潜水器的浮力会逐渐消失。
回忆当时的场景,付文韬仍然历历在目:“我们上浮到离海面还有1000多米时,一侧的压载体抛不掉,导致潜水器在海中既上不来,也下不去。我是主驾驶,当时心里一下子就想起了很多事。我跟同行的伙伴说,自己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不应该这么年轻就牺牲在这里。我就冷静地一边操作推力器,一边慢慢成功上浮。”
对于付文韬和同伴们而言,深潜科考并不仅仅是荣誉或者只有这一面,更多的是一种作为科学工作者的担当和责任。
“很多人问,下潜遇到那么多事情、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你们怕不怕?我们开玩笑说没什么好怕的,如果出了事情能处理那担心就是多余,如果真出了事再担心也来不及了。”但付文韬坦言,这只是玩笑话,“说实话还是挺担心的。对我来说,最难的其实并不是怎么去处理危机,而是我刚刚经历了这些事情后可能过几天又要继续下潜,那个时候对我们是最难的”。
这些困难与惊险历程让他深深体会到,要想做出成绩,年轻人要有年轻人的担当,同时还要有拼搏精神与创新。“人生难得几回搏”,就是他的座右铭之一。
“做事情不光要敢去做,还要开动脑筋将事情做成,更要发扬创新精神。深海驾驶尤其需要创新,因为我们没有固定的模式,遇到新问题、难题时一定要开动脑筋,发扬创新精神。”
多次深潜,让付文韬感受最深的是祖国的强大及党与政府的支持,“这是所有行业发展最坚实的基础。国家、集体、团队或者个人发展的背后一定要有精神支撑。我加入‘蛟龙号’团队工作十几年来,支撑我前进最大的力量就是载人深潜精神”。
对他而言,“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高峰”的载人深潜精神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前进最大的动力。“载人深潜的发展方兴未艾,是我国海洋战略的发展平台,我们欢迎更多的科学家能与‘蛟龙号’一起去到深海执行任务。”
 |
版权:《高科技与产业化》编辑部版权所有 京ICP备12041800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四环西路33号 邮编:100080 联系电话:(010)82626611-6618 传真:(010)82627674 联系邮箱:hitech@mail.las.ac.cn |